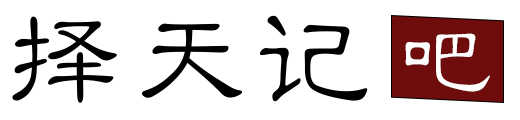青葉世界裡的學宮,不知日夜,裡面的人們也很難感受到時間的流逝,不知道外面的真實世界已經來到第二天。
時近正午,攤販們抓緊機會拚命地吆喝,以那些石柱為線,線外熱鬧到了極點,桂花糕的香味在食物的味道里最為清晰。
來看大朝試的民眾圍在離宮的外圍,議論著不時從宮裡傳出的最新消息,人們無法看到大朝試現場那些激動人心的畫面,情緒卻沒有受到影響,氣氛依然很熱烈,必須要說,這也有那些說書先生的功勞。
離宮外的街道上,隔著數十丈距離,便會有個茶鋪,鋪子前總會擺著張普通的桌子,穿著長衫或夾棉襖的說書先生站在各自的桌前,唾沫四濺,手舞足蹈,不停講述著此時學宮裡發生的事情,也不知道這些說書先生以及他們背後的老闆是與離宮裡的誰有關係,前一刻大朝試現場才發生的事情,下一刻便成為了說書的內容,而且竟沒有太多偏差
西南角有幢相對清靜的茶樓,裝飾頗為清雅,但今日這茶樓也不能脫俗,專門請了位說書先生在堂里坐著,而且還花了大價錢從離宮買了最新的消息,只見那位容貌清矍的中年說書先生一拍響木,說道:「話說曲江幽幽清能照人,諸位考生施展各自本事,或踏水渡江,或身化流雲,便將那位國教學院的少年落在了最後,一時間兩岸鴉雀無聲,都想看看那少年如何過江,誰曾響,只聞天邊傳來一聲鶴唳,白鶴歸來」
說到此節,這位說書人又是一拍驚木,將那些凝神貫注的茶客驚了一遭,才緩緩敘道:「當時曲江兩岸近百考生,皆如諸位一般目瞪口呆,諸位是被小老兒驚著,那些考生卻是被那隻白鶴驚著了。為甚?因為下一刻,那位國教學院的少年竟是二話不說,一掀前襟,便坐上白鶴後背,騰雲而上,向著對岸而去,真真是騎鶴下江南,此景何其奇也
茶樓里響起一片喧嘩的議論聲。
那位說書人笑道:「諸位不須議論,要知道參加大朝試的那些考生,無論是在宗派里還是在學院中,想必都見過仙禽異獸,但他們為何如此驚訝?因為沒有人想到,居然可以用這種法子過江,更令他們震驚的是,那隻白鶴可不是普通的白鶴,是我大周京都東御神將府的白鶴」
樓間議論之聲更盛,很多京都民眾都知道,東御神將府里養著白鶴,只是這些年見的次數少了,又有人想起了那件傳得沸沸揚揚的婚約,不由很是好奇為何那隻白鶴會願意馱了那位國教學院少年過去。」
「諸位若還沒有忘記,便該知曉,那隻白鶴已然隨著徐小姐遠赴南方聖女峰,為何會忽然出現在萬里之外的京都?莫非徐小姐真的認了那位國教學院少年作未婚夫?那在場的離山劍宗四位高足又會有何等反應?」
說到此處,這位說書先生輕咳兩聲,端起茶杯飲了口溫茶。樓中茶客明白這是何意,雖然有一兩位茶官惱火說道,這已是昨日的故事,怎好今日還說來騙錢,大多數人還是老老實實地隨了茶錢。
說書先生見著茶盤裡的銅錢數量,很是滿意,清了清嗓子,便開始繼續講述大朝試的故事,茶館們專心致志地聽著,沒有人注意到,一位戴著笠帽的中年人將杯中殘茶飲盡後,走出了茶樓。這名中年人的笠帽壓的極低,看不清楚眉眼,出樓後混進街巷裡的人群,不一時便消失不見。
過了段時間,這名中年人出現在離宮南四里外的一間客棧,他從懷裡掏出兩顆殷紅色的藥丸服下,痛苦地咳嗽了好一陣子,終於壓制住體內的傷勢,走到床上躺下,笠帽被推到一旁,黑髮里隱隱有兩處突起。
正午過後,所有茶樓茶鋪的生意都變得更好,只是說書先生講的故事則顯得不再那麼吸引人,因為大朝試文試的成績正式頌布了出來,各茶樓茶鋪的掌柜或夥計去離宮前抄了回來,開始對茶客們進行講解。
文試榜的最後一名是摘星學院叫張聽濤的考生,民眾們對這個名字毫無印象,自然也沒有太多議論,只是嘲笑了數句,又對摘星學院的辦學宗旨攻擊了一番便告罷了。軒轅破的名次很靠後,唐三十六排在第七,庄換羽在第六,槐院四名書生的成績極好,竟是全部進了前十,當然,人們最關注的還是最前面那兩個名字――苟寒食和陳長生分別排在首位和第二名,而且兩個人的名字旁都有備註:優異。
看著大朝試文試的最終榜單,看客們議論紛紛,嘖嘖稱奇,對著苟寒食和陳長生的名字指指點點,讚嘆不已。有外郡專程來京都看大朝試的遊客對此很是不解,心想即便排在前位,何至於被如此盛讚?
有京都民眾對這些人解釋,大朝試文試向來只排位次,只有極為優秀的考卷才會特意註明優異,這裡所說的極為優秀一般指的就是全對。苟寒食和陳長生的名字旁都注有優異,那麼說明他們的答卷堪稱完美。要知道這是非常罕見的事情,已經有好些年,大朝試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了。
那些外郡來的遊客這才明白其中道理,卻又有些想不明白,既然兩名考生的文試成績都如此優異,應該是全部正確,那麼又是如何分出的高低?為什麼苟寒食便要排在首位,陳長生卻只得到了第二名?
這個問題沒有人能解釋,那些見多識廣的京都民眾,對此也很是好奇,同樣不解的,還有離宮裡負責複核的那些考官。
文試主考官看著那個神情微寒、明顯是來找麻煩的教士,心想教樞處就算不忿陳長生沒拿到第一,又何至於表現的如此明顯?
但教樞處在梅里砂主教大人的統馭之下,一年來強勢異常,即便文試主考官的位秩要高過對方,依然不得不謹慎解釋。
「用語規範問題。」
他看著那幾名教樞處負責文試成績複核的教士,神情嚴肅說道:「別的方面都分不出來高低,但苟寒食的用語非常嚴謹規範,尤其是典籍相關的專用辭彙,就連避諱的疊筆都沒有錯誤,陳長生雖然答的沒有任何問題,但他的用詞過於古舊,按照大編修之後的標準來看,當然應該扣分。」
文試的成績已然送出離宮,公告天下,自然沒有再更改。得到優異評價的苟寒食和陳長生二人,成為所有人讚歎的對象,當稍後一些時間,進行對戰最後一輪的人選確認後,人們更是震撼異常,議論連連,因為那兩個人依然還是苟寒食與陳長生,這也就意味著,今年大朝試的首榜首名,必然要從這兩個人當中產生。
一位是舉世聞名的神國七律第二律,離山劍宗的少年智者,通讀道藏的苟寒食。一位是國教學院多年來的第一位新生,國教舊派重點培養的對象,徐有容的未婚夫陳長生,從名聲來說二人不相上下,能走到這步也證明他們各自的學識與實力,只是看好陳長生的人依然不多。
四大坊開出了最新的賠率,苟寒食是一又三分之一,陳長生則是七,相差非常巨大,甚至可以說是苟寒食穩勝的局面。
聽著樓下傳來的喧鬧聲,天海勝雪的臉上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,雖然先前他買了陳長生很多銀子,卻沒有想到那個國教學院的少年真能走到這一步,不過即便是他,也無法看好陳長生能夠繼續獲勝。
之所以到了最後也沒有人看好陳長生,是因為人們包括天海勝雪在內都知道,在苟寒食和陳長生之間橫亘著一道門檻。
那道門檻很高。
那道門檻與生死相關,更高於生死。
昭文殿里,主教大人梅里砂緩緩睜開眼睛,看著光鏡上顯示的文試成績榜單,靜靜地沉默了很長時間,然後他笑了起來,在辛教士的攙扶下艱難地站直身體,出殿向著清賢殿而去。他本只是想著借大朝試讓陳長生儘快成熟,卻沒有想到陳長生真地有可能摘下這顆豐美多汁的果實,沒有希望便罷了,既然希望在前,他自然不會允許任何人破壞,誰都不行。
離宮深處,神冕在桌上承受著殿上落下的天空,泛耀著奪目的光輝,神杖在台上反映著水池的倒影,彷彿是在深海之中,和這兩樣神器相比較,瓦盆里的那株青葉未免顯得有些寒酸,但教宗大人沒有看神冕,也沒有看神杖,而是靜靜看著那片青葉,沉默不語,有些出神。
他背著雙手,就像個年邁的花農。
不遠處便是那片清水池,木瓢在水裡輕輕起伏,彷彿扁舟,隨時可以盛水,那些水可以用來澆青葉,也可以用來落一場雨。
在離京都最遙遠的地方,有片莽荒的山嶺,嶺間森林綿延不絕,白霧繚繞,山路濕滑難行,而且異常安靜,如果不是山道間不時響起的篤篤聲,或者會顯得更加陰森可怕。
那些篤篤的聲音是木杖落在山道濕石上的聲音。
餘人撐著拐杖,艱難地向山道上行走。他和陳長生的師父,那位神秘的計道人正負著雙手行走在前方,似乎根本不擔心他跟不上來。
篤篤的聲音持續了很長時間,幽靜森林裡的雲霧越來越濃,裡面隱隱傳出很多細碎的聲音,彷彿有很多生物被杖聲吸引到了此間。
下一章:第一百七十章 八方候此一戰
上一章:第一百六十八章 打出自己的價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