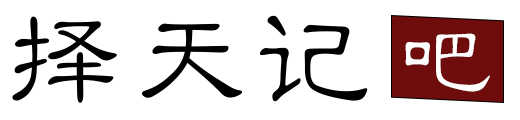綿密的風雪悄無聲息地落著,廢井四周一片安靜,北新橋的樹落盡了葉子,樹於上承著雪,就像是拿著槍的哨兵。聖后負著雙手,望向遠處國教學院的方向,沉默片刻後說道:「大朝試馬上就要開始了,有什麼想法?」
「教宗大人依您的意思把落落殿下接進了學宮,但再沒有別的表態。」
莫雨看著娘娘的側臉,輕聲說道:「其實依我看來,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把陳長生殺了,哪裡還會有這麼多麻煩。」
國教學院引起的風波,在聖后娘娘表態後,很快便沒有人再提起,但莫雨認為娘娘不是想藉此事表示自己的寬容與氣度,而是想等著隱藏在國教學院後面的那些人全部站出來――娘娘對世間所有事都瞭然於胸,此時來問她,想必只是想看看她的態度,那麼她的態度一定要足夠堅決。
出乎她的意料,聖后對她堅定甚至有些冷酷的態度沒有流露出任何欣賞的神情,反而唇角微翹,露出一抹有些嘲弄意味的笑容,說道:「如此行事何其無趣?再說把他殺了,你如何安睡?要知道枕頭和被褥上的味道終究是會散的
莫雨聞言慌亂,心想該如何解釋此事?
聖后沒有給她解釋的機會,轉身望向她,似笑非笑說道:「青藤宴那夜,是你把他關進桐宮的?」
莫雨忽然覺得今天的雪冷的有些透骨,哪裡敢有半分猶豫,應道:「是。
聖后沒有再看那口廢井,說道:「那是個好地方。」
莫雨再也不敢說話,恭敬而謙卑地低著頭,扶著她的手,向皇宮裡走去。
青藤宴那夜把陳長生困在桐宮,是她按照某位大人物的要求做的事情,至於陳長生為什麼能夠脫困,是不是真的進入寒潭底,遇見了那位禁忌,莫雨並不知道,也不敢去知道,因為無論如何,那都是她的原因。
娘娘沒有說對她的安排滿意或者說不滿意,但既然提起,便是警告。
大周朝野都知道,莫雨是世間權勢第二的女人,擁有難以想像的榮華富貴和薰天的權勢,她偶爾興起在眉間點抹紅妝,便能讓已經沉寂數百年的風潮重新興起,但她自己非常清楚,這一切都來自於娘娘的賜予或者說同意。
一旦娘娘開始懷疑她,她將會失去所有,將會死無葬身之地。
今天的風雪真的特別寒冷,她扶著娘娘的手指節有些發白,嘴唇也很蒼白,沒有一絲血色。
陳長生在國教學院的床上醒了過來。
他的臉色蒼白無比,嘴唇也很蒼白,看不到一點血色。
但他的身上到處都是血,肩與胸還有手指甲里,都是凝固的血,與雪白的被褥對比顯得格外刺眼恐怖。
看著屋頂,他睜著眼睛,沉默不語,直至五息時間過去,呼吸漸漸變得平穩後,他才緩緩側身,左手撐著床沿,慢慢地坐起身來。
在床邊,他又坐了五息時間,待心跳漸漸恢復正常,起身走到鏡前。
他望著鏡中那個渾身是血的少年,沉默了很長時間。
自己還活著,這種感覺真好。
在死亡邊緣走了一圈,然後重新回到人世間,這種感覺真的很好。
在地底空間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,他記不清楚了,只知道當星輝開始燃燒之後,他的神識便墜入了一道深淵,在那道深淵裡全部是燃燒的火焰、高溫的煙塵、恐怖的撕裂以及難以承受的痛苦,還有絕望。
他覺得自己彷彿做了一場夢,但他知道那是真實發生的事情。他現在還有些神思恍惚,下意識里抬起衣袖聞了聞,衣服上到處都是血漬,聞著雖然沒有什麼刺鼻的血腥味道,但對於性喜潔凈的他來說,這是很難忍受的事情。
他以為那些都是自己的血,依然無法忍受,於是他開始洗澡,洗了很多遍,才確認把所有的血全部衝掉,拿著大毛巾擦拭著身上的水珠,走到鏡前,準備把窗打開,放一些冬雪裡於凈的空氣進來。
走過那面大鏡子的時候,他忽然停下腳步,向鏡里望去。
鏡子里,那名少年**著上半身,看著很尋常。但他發現了一些很不尋常的地方。
這個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他這樣,對自己的身體了解的非常清楚――因為生病的緣故,他向來很注意這些方面――他記得很清楚,自己的左臂上方,有師兄給自己針炙時錯手留下的一道傷疤。但現在,那道傷疤沒有了,左上臂一片光滑。
這時候他才注意到,自己的皮膚變得細滑了很多,就像是初生的嬰兒。更讓他想不明白的是,自己明明受了這麼重的傷,身上卻找不到一道傷疤,就連以前留下的那些舊傷疤,也盡數消失不見,哪怕是最細微的也沒有了。
難道,這就是洗髓?從春天到現在,從遙遠的那顆命星汲取的星輝,在變成真元的過程里,有一部分順便幫自己洗髓成功?
他的心裡沒有生出得償所願的狂喜,因為他這時候很茫然,還處於心神恍惚的階段。
他看著鏡中的少年,皺著眉頭認真地思考著。
思考,是最能讓人冷靜清醒的事情。他越來越清醒,想起了越來越多的事情。直至最後,他終於想起來,自己昏迷前的那一刻,應該是在寒冷的地底空間里,在黑龍前輩的身前,怎麼醒來的時候已經回到了國教學院?
他看著微濕的毛巾,用手輕輕揉了揉,確認那些濕意是真實的。
他走到窗邊,望向冬林深處的皇宮城牆,心想從地底空間出來就是那片池塘,如果不是黑羊想辦法把自己送回國教學院,唯一有可能做這件事情的,便應該是那位中年婦人,那婦人究竟是誰?
先前在地底空間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?自己為什麼還活著?難道自己真的洗髓成功了?
他站在窗邊沉默了很長時間,終於做出決定,走回床邊,將被褥盡數掀開,盤膝坐上去,閉上眼睛,開始坐照內觀。
那道絕望而充滿的深淵,就是起始於他開始坐照自觀,現在他活了下來,卻毫不猶豫地再次坐照自觀,因為活著對於他固然非常重要,但他無法接受糊裡糊塗的活著,他需要弄明白自己現在究竟是什麼狀態。
神識進入他的身體,再次開始漫遊,只不過現在有了經驗之後,這種漫遊不再是無目的地觀察,更像是巡視自己的領地,沒有用多長時間,他的神識便來到了那片萬里雪原,在高空里望著地面。
他閉著眼睛,睫毛微微眨動,臉色蒼白如雪。
他很緊張,很擔心神識會像上次那樣,直接落到雪原上,再次燃起那般恐怖的大火。
即便意志堅毅如他,也絕對不想再次承受那樣的痛苦。
幸運的是,這一次他的神識沒有落下,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變故發生。
萬里雪原依然是萬里雪原,他的神識注意到,角落裡有一片雪原燃燒無蹤,化作了數十道涓涓細流在流淌,向著南方流淌而去,一路滋潤荒涼的原野,只是那些溪流太細,而且山脈斷裂,根本無法構成所謂的水系。
那些細流應該便是真元,因為他經脈的特殊情況,而無法像普通修行者那樣互相聯通,只能在小區域里存在。
陳長生睜開眼睛,開始思考。
他現在的情況和落落看似有些相似,實際上差別非常大。
落落的體內真元充沛至極,只是妖族經脈與人類相比,非常簡單,所以很難用來修行人類的功法。他的真元現在少的可憐,而且經脈盡斷,想要修行功法,更是困難。不過二者之間隱隱有某種相通之理。
關於經脈的問題,他這些年一直在思考,所以才會在短短數月時間裡,解決落落的問題,而解決落落問題的過程,實際上也是為他現在解決自己的問題做準備,對於自己如何修行,他早有安排。
是的,現在他體內的真元數量確實不多,經脈確實斷裂,但不代表他不能修行。
他走到窗邊,看著湖畔那片冬林里最顯眼的那顆雲松,調息片刻,握住短劍的劍柄。
鋥的一聲清鳴,短劍脫鞘而出,一道形散實凝的劍意,從二層樓的窗畔,向著那處飄渺而去。
鐘山風雨劍的第一式,起蒼黃。
但他沒有鐘山風雨劍的真元運行方式,而是用的自己教落落的那種模擬方法。
這是陳長生第一次使用真元,從這一刻開始,他開始稱自己是位修行者,或者修道者。
任何人如果有他一樣的經歷,此時或者都應該喜悅萬分,甚至激動的淚流滿面,但他沒有,就像剛才確認自己體內有真元流動時一樣,他平靜的不像是個十五歲的少年,而更像是個五百歲的修行前輩。
因為修行從來不是他的目的,只是他的手段,也因為他曾經無數次推想過現在的場景,想的次數太多,早已變得麻木。
隨著劍意破空而去,他的臉色瞬間變得蒼白,一聲輕哼,感覺有些痛苦。
遠處那顆雲松紋絲不動,窗外的石台破裂,數粒石塊像勁矢一般射進屋內,噗噗悶響里射進牆壁,有一顆擊中他的左臂。
按照教落落的那個方法,還是有些問題,要重新尋找通道,果然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。
陳長生搖搖頭,回身準備取藥粉來包紮左臂。
雖然他的真元微弱,難以真正地發揮出鐘山風雨劍的威力,但畢竟是以真元馭劍,那些被濺起的石子,比普通羽箭的威力也差不到哪裡去,能夠深入牆壁,自然能夠輕易地擊傷他的左臂。
以後應該更小心謹慎些,他在心裡對自己說道。
然後他發現,自己的左臂根本沒有受傷,連根寒毛都沒有斷。
(下一章爭取十二點前寫出來。)
下一章:第一百二十七章 腰纏十萬貫(上)
上一章:第一百二十五章 紅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