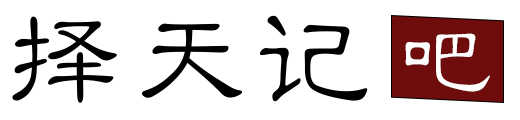就像徐有容忘記了昏迷中的陳長生一樣,白海也從來沒有在意過那名渾身帶著冰霜的年輕修行者。而且他此時正陶醉在天鳳真血帶來的迷幻般的至高快樂之中,沒有任何防備,於是竟被那隻手推離開來。
崖洞里一片安靜,白海看著陳長生,神情有些愕然,片刻後,他才明白生了什麼事情,覺得有些不對勁。
此時,他的唇角還殘著一滴血水,配上那張有些扭曲的蒼老的容顏,看著異常噁心,就在那滴血水快要滴落的時候,他醒過神來,有些慌張地用舌尖卷進唇里。對想要修行落陽宗秘法、突破通幽境的他來說,徐有容的每滴血都是至為珍貴的寶物,哪裡能夠浪費,只是這畫面未免更加噁心。
不知道為什麼,他覺得舌根有些甜,舌尖卻有些麻,心想難道這便是天鳳之血的味道?
就在這個過程里,陳長生扶著崖洞的石壁,艱難地坐了起來。他此時是如此的虛弱,似乎只要一陣風拂過便會再次倒下,如何能夠克敵制勝?
白海感覺到臉上有些麻痛,伸手摸了摸,現上面有些水漬,再望向陳長生的手掌,現他的手掌上亦是覆著冰雪,不由眯了眯眼睛。
毫無徵兆,他一指隔空點了過去,一道蘊藏著恐怖地火的氣息,直射陳長生。
陳長生似乎只是下意識里一掌拍了過去,掌前的空氣里卻瞬間結出一道冰鏡。
那道地火氣息,觸著這面冰鏡,嗤的一聲響,同時化作青煙散去。
白海的眼睛眯的更加厲害,看著他詭異笑著說道:「居然是雪山宗隱門的弟子,以為靠玄霜真氣,就能擋住我?
雪山宗是大6西北的一個宗派,相傳雪山宗的開派祖師擁有玄霜巨龍的血脈,自行開悟創造了一種功法,於是在西北極寒之地開山建派,全盛之時非常強大,無論是魔族還是中原國教正宗,都不願意輕意招惹,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,玄霜巨龍血脈殘留的越來越少,雪山宗也逐漸勢微,早在數百年前便已經附於離宮之下,而且也已經很多年沒有出現過真正的高手或是有前途的年輕弟子。
沒有人會低估一個曾經輝煌過的宗派,就像南溪齋分為內門外門一樣,很多大人物都知道,雪山宗也有隱門一系,只不過很少行走世間。落陽宗修行的是地火,與修行寒功的雪山宗天然抵觸,當年也曾經有過很多衝突,身為落陽宗長老的白海,自然對雪山宗非常了解,看著陳長生橫劍結出的冰霜虛鏡,一言便道破了他的來歷,同時心中的殺意也陡然間再提數分。
徐有容看著身前陳長生的臉,心想原來是雪山宗的隱門弟子,難怪修行的功法如此特殊。
她的視線有些模糊,卻可以清晰地感覺到陳長生眼神里的寧靜,明明局勢依然危急,陳長生依然傷重虛弱,可不知道為什麼,她忽然覺得可以放下心來,可以把後面的事情交給這個年輕的修行者了。
「沒有想到,居然能在周園裡遇到雪山宗故人之後,更沒有想到,我在神功告成之前,還需要多殺一個你。」
白海看著他詭異地笑了起來,說道:「好在這並不是太麻煩的事情。」
說完這句話,他化掌為刀,帶起一道火焰,毫不留情地斬向陳長生的面門。
不要說陳長生此時傷重虛弱,就算他完好無損,也不可能是這位落陽宗長老的對手。
他的醒來,似乎沒有任何意義,甚至可以說,他醒來的太不是時候。
他體內的真元已然枯竭,連短劍都無法握住,更不要說召喚出黃紙傘。
他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擋住這記火掌,唯一能夠做的事情,就是提起手掌,打向對方的臉。
他剛剛醒來,根本不知道生了什麼事情,也不知道這名老者是誰,只知道這名老者在做很殘忍噁心的事情,老者臉上的笑容有些僵硬詭異,笑聲陰森可怕,看著就不是好人,那麼……他就要打他。
下一刻,他可能就會被這名老者的火掌轟成廢渣,但他還是想打他,只要能夠打到對方那張陰險可怖的老臉,也算是沒有白醒這一場。
陳長生就是這樣想的,也是這樣做的。
但他沒有想到,自已的手掌居然真的能夠打中對方的臉。
啪一道清脆的響聲回蕩在安靜的崖洞里。
他的手掌打中了白海的臉。
雖然他揮掌的動作輕飄飄,看著沒有絲毫力氣,但這聲音卻很響亮。
耳光響亮。
白海怔住了,完全不明白生了什麼事情。
他的手掌還停留在半道,離陳長生還有一尺距離,掌緣那些恐怖的地火,正在漸漸熄滅,看著有些凄涼。
為什麼這個雪山派隱門弟子的手掌,能夠落在自己的臉上?為什麼自已的身體變得如此僵硬?為什麼自己體內的真元瞬間消失一空?只是瞬間,無數疑問湧進他的腦海,讓他驚愕恐懼。
下一刻,那些驚恐盡數在他的眼中顯現出來。他艱難地扭動脖頸,低頭望向陳長生身旁的徐有容,說出了最後一句話。
他的聲音異常沙啞於澀,語句斷續,難以成句,充滿了恐懼與絕望:「妖……妖……女……血……血里有……毒
說完這句話,他就死了。
落陽宗長老,通幽境巔峰的強者白海,就這樣死在了崖洞里。
他死的時候,身體已經無比僵硬,右手停留在空中,就連眼睛都無法閉上,眼中泛著幽幽的綠色,看上去就像一座沒有破皮的翡翠原石刻成的雕像。
這個畫面很詭異,很陰森。
下一刻,他的皮膚開始潰爛變化,潰爛卻沒有深入肉骨,只是生在表面,漸漸斑瀾。
有的斑瀾是美麗,有的斑瀾則是噁心。
陳長生覺得很噁心。
這時候他才明白,原來這名老者已經中了某種劇毒,只是不知道是何時中的毒。
先前老者臉上那副詭異的笑容,便是毒素作的原因,那時候,他的神識已經與身體漸漸分離。
這毒未免也太酷烈了些。
緊接著,他才想起崖洞里還有人,望了過去。
那名少女的衣裙上到處都是血污,快要掩去原來的白色,尋常清秀也快要被虛弱疲憊的神情掩蓋,眼神卻十分清冷。
他怔了怔,問道:「你沒事吧?」
……
下一章:第七章 人生若只如初見(一)
上一章:第五章 穿過她的黑髮的他的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