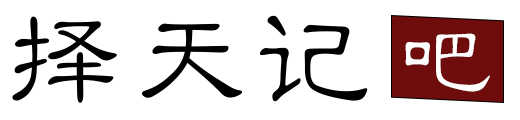有人看著那名口沫橫飛的擋鋪掌柜,惱火地喊道:「你哪隻眼睛看見的?」
那名當鋪掌柜以一種鄙夷的眼神看著他,說道:「我姐夫的外侄就在國教學院里上學,南溪齋那麼多弟子住在裡面,難道會看不到?不止是他,很多人都看得清清楚楚,聖女和陳長生站在樓上的窗邊聊天。」
街上變得一片安靜。
繁星閃耀的良夜,一對年輕男女站在窗邊,留下剪影,那是很美麗的畫面。
然而,沒有人願意為這樣的畫面喝彩。
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,人群終於醒過神來,震驚之餘生出很多不解。從去年開始就一直在傳,陳長生強行與徐家解除了婚約,雖說奈何橋一戰後,陳長生似乎變了主意,但……聖女難道就這麼輕易地原諒了他?她就這麼住進國教學院里,難道還真準備嫁給他?那徐府的顏面何存?以眼高冷厲著稱的東御神將徐世績,豈不是會變成一個笑話?
清晨時分,唐三十六、軒轅破、蘇墨虞在南溪齋弟子們的陪同下,進入小樓取了自己的行李,準備搬到國教學院東面去住。折袖是不會做這種事情的,他那些顯得有些寒酸的行李,被軒轅破提在了手裡。
他們站在緊閉的房門前,提著行李,看著有些落魄可憐。
「你總得給他留點面子,畢竟這裡是國教學院,他是院長。」唐三十六對著緊閉的房門喊道:「就算你是為了他的安全,也做的太誇張了吧,何至於讓南溪齋的劍陣把這裡圍著,還要把我們趕走?這裡是京都,可不是寒山,就算魔君也不敢來的。」
這間房是陳長生的住處,但他是在對徐有容說話。
一夜過去,南溪齋弟子和國教學院的師生們都知道她沒有離開過房間。
房門依然緊閉,沒有被推開,也沒有聲音傳出來。
徐有容坐在窗畔的書桌旁,看著床上熟睡的陳長生,不時伸出指尖輕輕揉散他因為痛楚而皺起的眉頭。
桐弓被她握在左手裡,散ˋ著淡淡的氣息,構成一道屏障,確保外界的聲音不會打擾到陳長生的休息。
但她能聽到唐三十六的話。
她知道自己帶著南溪齋弟子們忽然回到京都,必然會引發很多議論和震驚,但她不在意。
她讓南溪齋劍齋圍住這座小樓,甚至還要把唐三十六等人趕走,看上去有些不近人情,但那是因為以陳長生現在的狀況,想要得到真正的安全,那麼最好不要見任何人,她把他與唐三十六等人隔絕開,對雙方來說都是好事。
見著房門依然緊閉,唐三十六有些惱火,轉身向樓下走去。
走出小樓,踏上草坪,從那些隱而未發的劍意里走過,他們忽然看到湖畔的青樹下站著一位中年男子。
那位中年男子眉濃如墨,神情漠然,肅殺之意十足,衣衫隨晨風搖擺間,隱隱有股極淡的血腥味道。
葉小漣和十餘位南溪齋女弟子攔在這名中年男子身前,神情有些緊張,卻也不能拿對方如何。
因為他是齋主的親生父親,東御神將徐世績。
……
……
「回京了,怎麼不回府,卻住到了這裡?真是把我徐家的臉都丟光了!」
徐世績看著女兒清麗的眉眼間掩之不住的憔悴,沒有生出什麼憐惜的感覺,反而覺得有些不舒服,出府之前本來想好了見面後說話要儘可能柔和一些,聲音卻抑不住的變得冷淡了起來,寒意十足,如同訓斥一般。
湖畔的草坪很安靜,布帷隔住了遠處投來的探視目光,但南溪齋弟子們都聽到了這句話,心生不悅。
就算你是聖女的父親,又豈能用這種語氣說話?
有些年幼的女弟子,如葉小漣這般,視徐有容為神明般聖潔不可侵犯,心神微激之下,更是劍意與敵意一道漸生。
徐世績感受著那些敵意與劍意,再看著站在湖畔靜默不語的女兒,更是怒意難止,喝道:「難道?還敢弒父不成!」
徐有容轉過身來,看著自己的父親,說道:「父親這是說的哪裡話?」
她的聲音很平靜,很輕,很淡,所以這句解釋,聽上去並不像是解釋,當然,更沒有認錯的意思。
徐世績臉色變得更加難看,想起了很多從前的事情。
在很小的時候,徐有容一直是由太宰親自養育,他和夫人都插不了手,到了五歲時,徐有容體內的真鳳血脈蘇醒,被聖后娘娘接入宮中,又恰好遇著來京都觀陵散心的聖女,於是她便成為了兩位聖人的學生,那麼便更輪不到他來教育了。
世人對徐世績的評價並不高,但那主要說的是他的私德問題,比如對天海家的態度以及當初對陳長生的態度,誰都不會否認他的能力,絕對可以配得上大周神將。在北方的雪原里,他曾經立下過不少戰功,他治軍極嚴,治府亦如治軍,無論是雪關里家世背景特殊的偏將,還是府里的老人,在他的面前都噤若寒蟬,不敢有任何反對的聲音,然而……他卻沒有辦法管自己的女兒。
因為他沒有那個資格。
這個事實對任何父親來說,都不會帶來任何愉悅的感受,只不過徐府既然要享受徐有容帶來的光彩與好處,那麼便必須承受這一切。
可是,他終究是她的父親,她是他的女兒,他以為她總要給自己一些尊敬,就像過去那些年一樣。
然而,今天清晨在國教學院湖畔,他才知曉,原來自己的那些想法不過是自欺欺人。
「好一個不肖女……」
徐世績聲寒如冰,右手微顫,似乎下一刻便會打到徐有容的臉上。
徐有容平靜地看著自己的父親,她當然不會還手。
南溪齋弟子們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,尤其是葉小漣等少女更是握緊了劍柄。
便在這時,一個瘦瘦的老人來到了場間。南溪齋的劍陣,對這位老人來說起不到任何作用,不是因為老人很強大,而是因為他是大周皇宮的太監首領,是深受聖后娘娘信任的近臣,而且他到來時,高高地舉著一封聖旨。
「娘娘說,不要因為這種小事,影響了你們父女之間的感情。」
太監首領看著徐世績面無表情說道。
聖后娘娘這話明明是對兩個人說的,他卻只看著徐世績,意思自然非常清楚。
這是警告。
徐世績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,心想這等迕逆之舉,難道還是小事嗎?
她究竟是我的女兒,還是娘娘你的女兒呢?
這些只能在心裡想著,表面上他不能有任何流露,甚至還要強迫自己的臉色平靜些。
他看了徐有容一眼,沒有再說什麼,轉身向國教學院外走去。
他的背影顯得有些落魄,看著就像是被趕出獅群的老獅子。
徐有容看著父親的背影,沉默不語,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
太監首領望向她,神情頓時變得謙卑了數分,低聲說道:「娘娘請您入宮。」
徐有容接過聖旨,說道:「等我片刻。」
……
……
「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她,而且在國教和她之間,我不可能站到她那邊。」
陳長生拒絕了與徐有容一道入宮的想法,這句話里的她,自然指的就是聖后娘娘。
徐有容沒有說話,她其實也很清楚,如果帶著陳長生入宮是件極冒險的事情——她知道那位胸懷天下,甚至更加的聖人,對世間的那些情感是何等要的居高臨下、漠視,聖后娘娘這兩年沒有對陳長生做什麼,可能是因為要考慮離宮方面,也可能是因為一直無法確定,現在各種線索都已經指向了十數年前的那件懸案,誰也無法保證,她在皇宮裡見到陳長生後,會發生什麼事情。
「你不用擔心我。」陳長生看著她的神情,知道她在想什麼,說道:「入京前你才施展過一?聖光術,昨夜師叔用聖水替我浴身,又多了一道屏障,短時間裡應該不會有問題,而且南溪齋的劍陣不是會一直在外面?」
徐有容沒有再說什麼,就此離去。
站在窗畔,看著漸漸遠去的她的背影,陳長生的神情變得有些沉重。
他比誰都清楚自己現在的情況,比她清楚,比教宗清楚。
他的經脈盡數被星輝燒蝕而斷,沒有辦法修復。
他的神魂隨著鮮血滲進骨肉里,無計可以消除。
他的傷勢現在看似被壓制住了,但生機正在不斷地流失。
他的身體與命運早就已經千瘡百孔,破爛不堪。
換成別的人,在這種時候,只怕早就已經失魂落魄,但他卻依然保持著平靜。
他直接走下小樓,向布縵那邊的國教學院走去。
徐有容不在,南溪齋的弟子們根本沒有辦法阻止他離開,劍陣雖然可怕,但又如何能夠落在他的身上?
國教學院的主樓外有很多雕像,還殘留著十幾年前那場驚天之變的痕迹,噴泉已經修好了,石獸像卻還有些殘破。
他看著蘇墨虞說道:「今後這裡可能就要交給你了。」
他望向唐三十六說道:「如果可以的話,能把回汶水的時間推遲一年,那是最好不過。」
接著他望向軒轅破說道:「你不要總想著傷已經好了,還是得堅持吃藥。」
最後他望向折袖說道:「我沒辦法繼續給你治病了,但我會爭取儘早把醫案拿出來,你千萬不要放棄治療。」
……
……
(前面三天,和朋友們一共四家開車去伊春玩了一趟,距離確實挺遠,很辛苦,但是很開心,真的很建議大家多出去玩一下,河山之美在書上無法看的太真切,雖說工作都忙,生活都累,但千萬不能放棄享受,老話說的對,生命就應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。)